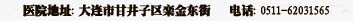晚宴
作者:甜河
如何步入逸事的黄昏?我用一次奉献一生。预感失败的时刻,扇子的细褶还在无穷变多。告诉我,弓箭的足尖在哪着落?孑然如衣冠楚楚的饮器。哦,这纤细的梅花饱含远景之泪,怎能缭绕于我。它旋转,旋转,旋转等待迷人的舌头分食风景。活着,或如扇子的醉态:在你耳廓之后,引吭拨动嘹亮的丝绸。为什么,你就要快乐得发颤,任凭晚风的绒毛细细消磨?任凭一群人带来另一群人,而美会衰竭,会在耳中发出嗡鸣的玉响?此刻,轻微失重的时刻,毫无来由地我们都在渴望着受伤。
诗人简介:
甜河,92年生,现就读于同济大学哲学系。一位原教旨的米老鼠主义者。曾获第四届光华诗歌奖,有少量诗作幸存于世。
网友diaspora点评
“如何步入逸事的黄昏?”开头第一句诗人即以问句掷明了自己的意愿——似乎除了“步入逸事的黄昏”,再没有什么是眼下关心的,要紧的,以及可以选择的。紧接“我用一次奉献一生”更像是一句如临命涯时的交待,凿出诗人对于走向黄昏的使命感。面对这唯一的、最后的黄昏,诗人将倾其所有赋予其“晚宴”的繁荣。“预感失败的时刻”,诗人在一初始已经接受了“晚宴”之后一切归亡的预设结局,但在此时此刻,事物之美仍自发地无可抑制地向繁荣变化(“扇子的细褶还在无穷变多。”),这便是事物的发展规律,像其后注定的衰落、终止一样(“弓箭的足尖在哪着落?”)。命运面前,每个人都面色苍白,即便迅猛如弓箭,也会在势能减退后成为足尖般轻盈无害的东西,成为落地的“零”。
那么诗人走向黄昏之时,心中就全然慷慨而无忧伤吗?并非如此,第二段对于“孑身”和“落梅”的描写,饱含着一种纤细得近乎柔情的哀伤(“饱含远景之泪”,“远景”一词中难道不是蕴含着倒退、逝离?),一种缠绵般的惋惜与难舍(“缭绕于我”、“它旋转,旋转,旋转”)。“等待迷人的舌头分食风景”,这纤细如落梅的美丽事物,必将为更多的嗜美者所享用,“晚宴”的“宴”之含义得以昭示。
第三段,“扇子的醉态”呼应前文中“扇子的细褶还在无穷变多”,把无穷变幻的丰饶喻为一种“醉”,这也是“活着”最为迷人的地方。说到“醉”,酒盛在饮器当中,因而“扇子”与第二段中“衣冠楚楚的饮器”亦是互为照影。“丝绸”给人的感觉光滑,是人世间多么无忧无虑的事物,诗人以此比拟乐器、乐声(但应想到,正像发出越高声调的弦越细,“嘹亮”者更靠近纤弱和危险)。于是“你就要快乐得发颤”,以“引吭”,以“快乐”去效行那生之最高处的战栗迷狂!“你”是谁呢?我想诗人此处可能揭露了她的一位同谋,也有可能是借“你”来投射自身,正如“扇子”与“饮器”的关系。“晚风的绒毛细细消磨”再度提醒了我们时间——如今黄昏已经褪变成了晚上,“细细消磨”中我们同样能感觉到时间在发肤上的微弱流耗(以及多褶之扇徐徐摇动的息吐)。
当这场晚宴消逝后,还会有新的主人新的来客筹造新局吗?“一群人”总会“带来另一群人”,这也是大命运的形态。而“美”会不会在今天就此“衰竭”,还是“会在耳中发出嗡鸣的玉响?”诗人似乎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,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参见这大命运中的一小部分,于是,她和晚宴上其它的宾客共同等待着,略带兴奋,魂不守舍(“轻微失重的时刻”,灵魂的迷狂被唤醒)本能般地(“毫无来由地”)渴望着亲历命运的来临,即便那是“受伤”。
最后再略谈诗人的语言,列举几处:“逸事”一词原本逸乐曼妙,一定程度上为随后出现的“奉献”一词减重;“弓箭”原本威武,而用“足尖”“着落”去形容它的触地,为其赋予阴柔的气息,令人想起古时游宴中用以娱乐的“小弓”;而像“细褶”、“足尖”、“衣冠楚楚”、“丝绸”等词语都用较为一致的声色整饬出诗人的美学意愿,使人联想起辞赋中的丽句(毫无疑问,它们都是逝者之歌),同时,这一美学也紧扣着“晚宴”之美——精致,雅艳,清婉,又如瓷器般易碎,恰与“晚宴”之脆弱空浮吻合。诗人以己身轻薄的骨架,与难御的大命运形成对比,也如那婉转梅花,以最轻的体态,写出一种哀楚却神圣的前往。我想,用“美”的形式去完成对于“美”的殉道,便是对“美”的最大敬重。
(点评网友:diaspora)
在编委会评选中,网友diaspora的评论最终入选,她将获得元点评费用。
同时感谢“灯芯、而已丶、gxh砥砺前行迎曙光”等网友的参与,也在此展出其优秀点评,以资鼓励。并希望其他网友继续参与评诗。
网友:灯芯
甜河的感触神经敏锐到了切肤疼痛的地步,她仅宴席之间便感受到了崇高命题美的衰竭。基本所指的是,《晚宴》表现的是杯盏饮器间庸常却又衣冠楚楚的应酬。在这个表现过程中,预感到宴席的无聊和俗套的“我”将赴宴放大到奉献一生的地步,可谓是一种纯烈心绪。无可奈何只好赴宴。在宴席间失神,看着饮器上的梅花犹如自我等待被世事分食,不禁自怜,席间的他人却“快乐得发颤”,可以消磨屋外自由的晚风,“我”感到不公平,为什么你就要这样快乐,我却要陪着你消磨?在这个过程中人群幻变仪式照常,酒话都在耳朵里滥觞,美早已在频繁的交际中衰竭。“我”更像清高的居士,但最后一句是一种强力回拨,越出了“我”高处不胜寒的视线,看到了“我们都在渴望着受伤”,提升了这首诗歌的层次,“我”走出了顾影自怜,走向了他人的生存境遇——我们都不免厌弃这种交际,但是又迫不得已。不得不提的是,在言说崇高命题变得虚无的后现代语境中,甜河由宴席间的出神走向美,走向恒久,既有自己诗人的灵锐,也有女性纤细的敏感。呈现这种微妙的心绪,甜河的语言自然属于上乘了。《晚宴》的语言游弋与崇高和灵秀之间,“预感到失败的时刻”,无疑是一种里尔克式的崇高慨叹,而“晚风的绒毛细细消磨”则是李清照式的细微感受了,这二者构成的张力则是甜河诗歌的最大特点。不可否认这首诗歌具有“怨”气,不过甜河写作早就有了古今中国,各门各类的视野,超脱“怨”,进入“美”,怜悯“生活”等更坚硬和广阔的风景已不是难题。
网友:而已丶
第一节表明的是诗人对晚宴的态度,定义了本诗的感情基调:“如何步入逸事的黄昏”,是否真的是逸事的黄昏,一场晚宴一回应酬一次妥协,这可能不是第一次,但我每次都幻想它是最后一次。既非我愿,结局自然不难预知,那又怎样,置身其中的我早如同上弦的箭,射向哪里落点何处又如何能够自制。第二节详细描述了在晚宴上诗人的状态和处境:置身其中又格格不入,看着热闹和明亮充斥四下张牙舞爪,于我而言近在身旁却远在天边,只是静静地看着,他们觥筹交错他们乐在其中。我只是如同一只“衣冠楚楚的饮器”,一杯一杯麻醉自己的身体。第三节是诗人内心走向妥协的挣扎与嘶吼:他知道其实这就是人生,没有绝对的清醒和理想,少不了一场又一场宴会的拼接,谁都无法逃脱,或许就该如“扇子的醉态”,半梦半醒,随波逐流,逢场作戏。第四节宴会达到了高潮或者说是尾声,酒过数巡,举杯间迎来送往数波熟悉的人,熟悉人介绍的人,甚至不熟悉的人。耳中“嗡鸣的玉响”和身体“轻微的失重”是饮酒后的丑相。在诗人看来,宴会的本质并没有什么高大上,不过是一群衣冠楚楚的人用酒精互相伤害抑或自我麻醉罢了。
网友:gxh砥砺前行迎曙光
人生如同晚宴,真爱何时能求这首《晚宴》,总体感觉有一股黛玉式多愁善感气息,全诗氤氲着诗人对爱情的失意而感到锥心之痛,进而对人生失去了淡定与自信而彷徨踟蹰。标题“晚宴”匠心独运,一词道破这是“黄昏”的宴会,表面隆重,却“预感失败”之失意落寞。虽然“我用一次奉献一生”倾吾所有,心中的惆怅、皱褶犹如“扇子的细褶”无休止地加添,何时能见曙光?于是诗人诘问苍天:“告诉我,弓箭的足尖在哪着落?”暗示“我”的意中人非他又会是谁呢?“我”便忐忑不安起来……第二小节诗人坦言自己孑然一身,无所依傍:爱情失意使她灵魂挫伤,哀怨自己虽“衣冠楚楚”一个冷美人,却仿佛一只可怜高挑的酒杯,只能对之伤感,借酒消愁。梅花傲雪、高洁、坚贞,可她还不是缭绕于人,东旋西转,等候意中人用“迷人的舌头”来接纳自己而共度人生嘛!这也许是梅花作为花的宿命与归宿吧?难怪诗人把自己比作“这纤细的梅花”隐忍“饱含远景之泪”之痛呢!故此,诗人慨叹了对人生的无奈。人生如同“扇子的醉态”:别人在你耳边高论、美言、蜜语几句,为什么就能使你神魂颠倒,高兴得“发颤”而乱了阵脚?为什么要任凭自己渐渐磨蚀自己的清醒与意志?最后一节是诗人在感情受创之后的呻吟与呐喊。别看那一群群一对对男男女女,来来往往,眼花缭乱,其中能有几对是找到了真爱并持守了真爱?因为,外表的假象,凑合的爱情,闪婚试婚的追捧、泛滥,只能是“美会衰竭”的可悲结局,岂会是真让人感受到幸福的光芒?那只能是在“耳中嗡鸣”的一种幸福幻觉罢了,这样的“爱情”只能给人带来飘飘然的“轻微失重”,使人坠入不知不觉的伤痛之中,难以自拔。然而,末尾“我们都在渴望着受伤。”是诗人在揭示人性的晦暗之处:即使像自己对待爱情有些理智和醒悟那样,人们也不愿再去纠结于情感与理智的漩涡之中,明知这场爱很可能会给双方带来“受伤”的后果,却仍然‘毫无来由地’身不由己、情不自禁地去“渴望”占有对方的肉体与感情。这是人性中善与恶、美与丑、光与暗的较量,看谁能自重,看谁能得胜。遗憾的是,诗人也许太年轻,涉世较浅,没能给出果敢而正确的抉择来。总之,本诗描摹情感丰富,用词细腻温婉含蓄,物象意象选取得当贴切,乍看有些晦涩难懂,细细咀嚼有味,总体格调略显忧郁哀伤,但瑕不掩瑜。(安徽高绪华)